 |
 |
 |
 |
 |
 | ||||||||||||||||
 |
 |
 |
 |
 |
 | ||||||||||||||||
 |
 |
 |
 |
 |
 | ||||||||||||||||
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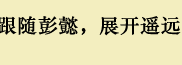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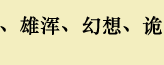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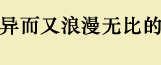 |
 | ||||||||||||||||
 |
 |
 |
|||||||||||||||||||
 |
 |
||||||||||||||||||||
| 我是一个另类作家。 我倒不是要标榜我有什么与众不同,而是我一天到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魑魅魍魉的幻想世界里不能自拔。这是我的职业,我是一个职业的幻想小说作家,我写幽灵,写妖孽,写大树成精,写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发生过的凄美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。 这个世界也让我战栗,但全中国只有我这样一个专写幻想小说的作家,我命中注定是要写下去了。 不过,我与生俱来拥有这个天赋。不是说我有一种第六感,看得见死而复生的人或是飘飘欲飞的精灵,我看不见,但我天生就有这种幻想,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之间有一条裂缝的话,那么我,就是双脚跨在那条裂缝上的人了。只要我闭上眼,现实世界的人、声音就会遽然遁去,梦魇般的幻觉就会把我紧紧裹住…… 看看我都写过一些什么样的小说吧―― 《与幽灵擦肩而过》讲了一段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,麦垛是一个在日本漂泊多年的留学生。在发现妻子移情别恋之后,他陷入了极度的孤独和抑郁之中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邂逅了美丽善良的雪女,并与之产生了纯真的爱情,可到头来却发现雪女乃是一个缢死在山林中的幽灵…… 《妖孽》说的是一个叫妖湖的地方,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,说是有一个名叫鹅耳的少年将一头凶残的妖孽压到了湖底。几千年过去了,这头妖孽复活了,它开始寻找投胎转世的那个少年,它要血耻。面对怪物的挑战,一个十岁的人类男孩挺身而出了…… 尽管有自我吹嘘之嫌,我还是不得不承认,这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好看的小说,只要你读了一行,就一定会爱不释手。 然而,它们的写作却是让我痛苦不堪的。 一部长篇要写一年,像《妖孽》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我写了整整两年。也就是说,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,我要陷在那个人鬼不分的世界里不能自拔,我要虚构一个个诡异的故事,虚构出一个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噩梦,我还要自圆其说,明明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,非要把它编得像真的一样。 有时,我都不知自已是在幻觉里,还是醒着? 我透不过气来了。 一天, 当我在镜子里面看到了我那张快要疯了的脸时,我知道,我该上路了。 我必须逃离这个世界。 | |||||||||||||||||||||
| 如果说我上路的初衷还只是为了逃避写作的话,那么到了后来,我则是为了写作而上路了。 我一路流浪,去了很多人迹罕至的地方。 那里是摄影师的圣地。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与摄影师们同行,但大师们风餐露宿一个月,有时仅仅是为了拍到一张片子。我没有,我不会为了拍到一张所谓的大片而欢呼雀跃,我会细心地记录下一个个被他们遗漏的局部,比如,几片红叶、一头小虫或是与我们同行的藏民的一个表情。当然,还有我的感悟。 在接近旅行的尾声,我突然有了一个灵感,一种创作的欲望直抵我的胸臆――除了幻想小说,我还可以用照片和文字进行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! 我把它叫做摄影旅行笔记。 我去了青海,去了甘南,去了稻城,还去了残留着一片胡杨树的额济纳,写了厚厚的四本书:《独去青海》《三上甘南路》《约群男人去稻城》《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》。书是全彩的,纸是特种纸,每本书除了凄美到了极致的文字,还有几百张大大小小的照片,我不记得国内有那位小说家曾经出过这般美丽的书了。 如果一定让我把书中的照片与文字做一个比较的话,文字肯定是胜出一筹了。我是把它们当成幻想小说来写了,至少这四本书里,弥漫着一种幻想、诡异而又无比浪漫的气氛,书中我还写了许多男人的故事,比如,我写了一个男人在胡杨林里独自唱情歌的故事,那是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―― 有一个男人,每年都会独自一个人千里迢迢地去看一片树。 已经连着去了五年。 那片树总是让他双泪长流。 那里不是他的故乡,那里他一个亲人也没有。 树下并没有埋葬着谁。尽管这个面容冷峻的男人总是选择一个秋风乍起的日子去看它们,但落叶飘零的树下,并没有长眠着一个他心爱的女人,那里也并没有发生过一段什么凄美悲凉的爱情故事。 他来,只是为了那片让他魂牵梦萦的树。 那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,风沙弥漫,贫瘠干涸得近乎寸草不生。然而,就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,有一个名叫额济纳的小地方,却长着一片“活着,一千年不死;死了,一千年不倒;倒了,一千年不烂”的胡杨树。他每年都来,他说,以后他老了,哪怕是风烛残年了,爬也要爬来…… 不过,顺便说一句,也别以为我的摄影水平差到了极点,上海的一位女记者在一篇专访中这样写道:“彭懿照片拍得好早就听说了,但看到这四本书的时候还是有些吃惊,因为还不曾见到哪个作家有如此的摄影功力。” 还要再顺便说一句的是,我是摄影协会的会员。 我是甘肃现代摄影协会的会员,终身会士。 不知出版了这四本摄影集,中国摄影家协会会不会接纳我?那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个心愿了。 | |||||||||||||||||||||
| 我们究竟是误入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呢? 是迷路,还是绝路? 亦或是条天路? 一切都是从这个晦暝阴雨的早上,一个扑朔迷离的藏族女孩搭上了我们的车子以后开始的。 当我们上路时,发现车里多了一个藏族女孩。 女孩长得还算姣美,红衣红袄,还系着一块红头巾。诗人问她:“我们去郎木寺,你去哪?”女孩含笑不语,只是用手往前面一指。 我们没觉出什么不祥,就上了路,其实这时我们已经走错了路。 一开始走得还顺,但走着走着,就不对了,这路崎岖坑洼得简直像是一百年没有车走过了。等我们清醒过来,发现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五个小时了,按理说,玛曲距离郎木寺只有80来公里,至多,三个小时也跑到了,可现在郎木寺连个影子也不见,而且越走越有一种远离人世的感觉。诗人终于嚷嚷起来:“我们这是走哪儿来了?” 还有更跷蹊的呢! 这一路上我们不知碰到了多少条旱獭,数都数不过来。开始,它们还在车边逃来逃去,后来干脆不逃了,这些肥硕的小东西不是在它们自己的窝边,就是在路边用后腿踮起身子,排成一排向我们张望。吓得我们头皮都发麻了,旱獭成精了吗? 不过,我必须承认,景色是越来越美了。 花田一片接着一片,还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水沼。但这景色美得有点离谱,有点让人发?,有点让人疑心这不是人间的景色。 车外的雨逐渐大了起来。 当雨雾中显现出一个小村庄的轮廓时,一直沉默不语的女孩突然叫了起来。她下了车,冲我们笑吟吟地招招手,就消失在了滂沱大雨中。我想追出去,把她拽回来,把这一切都问个明白,可倏忽之间,不单是她、连那个海市蜃楼般的小村庄都不见了! 小村啊小村,莫非说你是一个天堂小村? 女孩啊女孩,莫非说你把我们带到了天堂的门口? …… |
|||||||||||||||||||||
| |||||||||||||||||||||
|
| |||||||||||||||||||||